造紙術的發明者究竟是誰?東漢蔡倫還是另有其人?
更新時間:2024-08-19 10:52:00作者:佚名
造紙術是我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造紙術是誰發明的呢?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是東漢宦官蔡倫發明的。主要依據是《后漢書·蔡倫傳》的記載。書中說:“自古書籍、契約都編在竹簡上,用絲(即按書寫需要剪下的絲織物)制成的,稱為紙。絲貴,簡重,不方便人用。蔡倫想出(發明、創造)用樹皮、麻頭、破布、魚網等做紙。元興元年,進獻給皇帝。皇帝很滿意他的本領,從此人人都用,所以世人就稱它為‘蔡侯紙’。”所以,后來的中外一些著作都尊東漢蔡倫為紙的發明者,并把他向漢和帝劉肇進獻紙的公元105年,作為紙的誕生年。

但自從1933年,已故考古學家黃文弼在新疆羅布泊地區發現一張西漢中期的古紙后,對造紙術的發明就出現了不同的看法。1957年5月8日,在陜西省西安市郊灞橋磚瓦廠建筑工地的一座古墓中,發現了88片古紙碎片。這疊古紙在三面銅鏡下墊得厚厚的,雖已碎成碎片,但邊緣并未完全腐爛。這一發現引起了研究者的興趣。據考古學家考證,這座墓葬的年代不晚于漢武帝五年(公元前118年),因此灞橋紙的年代大致可以判定在公元前118年之前。這個時間比蔡倫發明紙的時間早了200多年。此外,1973年至1974年,在甘肅漢居延遺址還出土了兩片西漢晚期的麻紙。尤為值得指出的是,1986年6月至9月,甘肅省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員在天水馬灘西漢墓中出土了一張地質圖。該紙長5.5厘米,寬2.6厘米。這張新發現的西漢紙質地圖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的紙質實物。這些都有力地證明了古代中國在西漢早期就發明了可用于書寫和繪畫的紙。

另外,史籍中早在蔡倫之前就有一些關于紙的記載。如《三福九世》中說:魏太子劉據鼻子大,漢武帝很不喜歡他,江充給他出主意,教他再去拜見武帝時“用紙捂住鼻子”。太子聽了江充的話,用紙捂住鼻子,進宮拜見武帝,漢武帝大怒。這幅畫作發生于公元前91年。再如《漢書·趙后傳》中記載:漢武帝寵妃趙飛燕的妹妹趙昭儀想殺曹魏的宮女曹魏,便派人送來毒藥和“和體書”,逼曹魏自殺。東漢應劭說:“和體”就是“薄小紙”(后稱絲棉紙)。又如《后漢書·賈逵傳》載,公元76年,漢章帝令賈逵選二十人講授《左傳》,“將經疏以簡紙,各授一人。”以上有關紙的文獻記載,均在公元105年蔡倫向漢和帝進獻紙之前。

否認造紙術為蔡倫發明的同志認為:“造紙術是西漢勞動人民發明的。東漢勞動人民在繼承了西漢造紙技術后,又加以改進、發展和提高。和帝時,尚方令蔡倫組織少府尚方作坊,調集充足的人力、物力,督造了一批比前代更為精細的紙張,并于元興元年進獻皇帝西漢時發明的農具,經推廣,‘從此天下皆用之。’”這是爭論中的一種意見。

另一種觀點則堅持認為蔡倫是我國造紙術的發明者西漢時發明的農具,因為“據漢代許慎《說文解字》對紙的解釋,蔡倫以前的古代文獻中提到的紙,都是用蠶絲纖維制成的,實際上并不是紙,而是漂白蠶絲的副產品。從古至今,要制成一張中式的植物纖維紙貝語網校,一般要經過剪紙、漚紙、制漿、懸浮、抄紙、定型、干燥等基本操作”。但灞橋紙并不是真正的紙。理由是“從外觀上看,它的紙腹松散,紙面粗糙,厚薄差別很大。用實體顯微鏡和掃描電子顯微鏡觀察后發現,纖維和纖維束大多較長,說明它的切割程度較差,是纖維自然堆積而成,沒有經過剪紙、制漿等基本造紙操作,不能算是真正的紙。”也許只是漚制紡織物碎屑,如亞麻、線頭等纖維的堆積,由于古墓中銅鏡下鏡身長年累月重量的壓力,結成了片狀。此外,其他所謂的西漢古紙也十分粗糙,充其量只是紙的雛形。蔡倫及其工匠在前人浮制、制作雛形紙的基礎上進行了總結和改良,將紙的生產從原料和技術上轉移到了獨立工業的階段,并用于書寫。誠然,“蔡倫紙”并非蔡倫一人所制,但如果沒有他的“創造力”,僅憑尚方工匠也不可能造出這種植物纖維紙。因此,即使在雛形紙出土的今天,將蔡倫視為我國造紙技術的發明者或代表人物依然是正確的,有著充分的歷史依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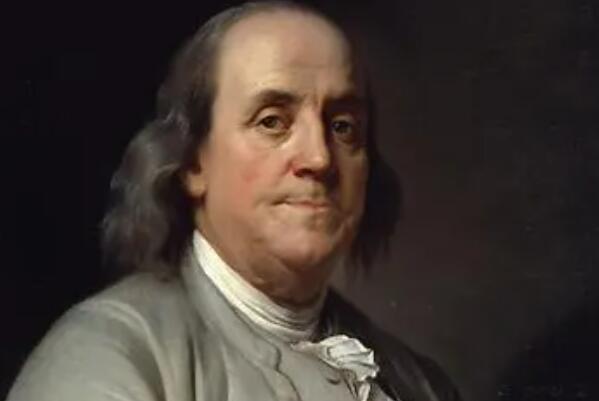
另外,書中引用的《后漢書》中有關蔡倫造紙的記載,主要取自劉震的《東莞漢記》。劉震與蔡倫是同時代人,應有可信度。從記載中可知,蔡侯紙既可作為進貢品,又可代替絲綢書寫,紙的質量必定達到了一定的水平。
一些學者也認為,灞橋紙是否為西漢產物也值得進一步考證。他們提出的理由是“在埋葬者的生活時期不能準確測定之前,對古紙的制作時期很難做出令人信服的科學判斷。而且墓葬土層擾動,曾受過外界因素干擾,不能排除后人偷運進來的可能;長馬王堆,同樣是一座漢代墓葬,墓主姓名可查,史料可靠,出土文物如此豐富,卻除了數千枚竹簡和絲織古紙、畫作外,竟無一張麻紙。”有研究者還在出土的灞橋紙上辨認出類似楷書的字跡,與新疆出土的東晉寫本《三國志·孫權傳》上的字跡十分相似,因而認為灞橋紙可能是晉代產物。